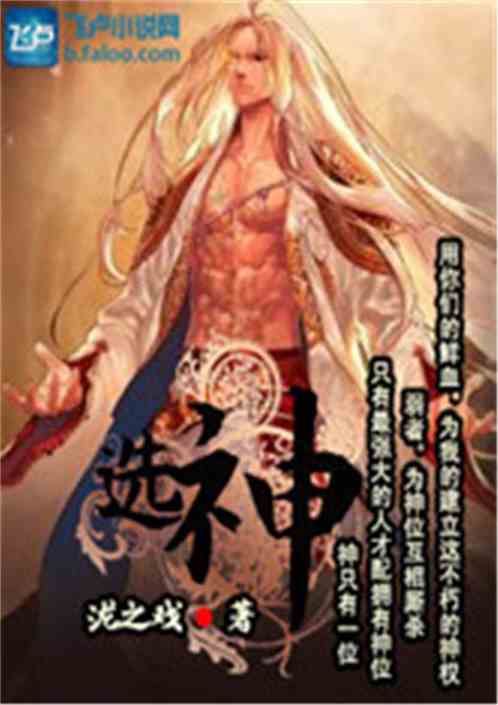《恐怖游戏》3 免费试读
国歌一结束,我们就被监督了。我不是说戴着手铐什么的,而是被治安警察看着,从法院大楼的前门走过。之前的一些“贡品”可能是逃了,虽然我没见过这种事。
进了门,我被带到一个房间,独自留在那里。这是我见过的最华丽的地方,厚厚的地毯,天鹅绒的沙发和椅子。我知道天鹅绒,因为我妈妈有一个用它做的领子。我坐在沙发上,忍不住用手来回倒鹅绒,这样可以让我平静下来,迎接下一个时刻。很快,我们就要和我们爱的人说再见了,我不能分心。我不能红着鼻子肿着眼睛走出这个房间。哭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火车站会有更多的摄像机等着我们。
妈妈和姐姐先来。我上前拥抱了波莉。她爬到我的膝盖上,搂住我的脖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像她蹒跚学步时一样。我妈妈坐在我旁边,拥抱了我们俩。我们有几分钟没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告诉他们要记住什么,这是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做的了。
我告诉他们波莉永远也不会得到食品券。他们生活节俭,靠卖波利羊生产的羊和奶酪以及母亲在“裂区”开的小药店生意就能生存。盖尔会采摘妈妈种不出来的草药,但一定要详细告诉他草药长什么样,因为他没有我熟悉。他还会给它们带来猎物——大约一年前我们达成了协议——它们不应该得到奖赏,但它们必须感谢他,给他一些羊或药物什么的。
我不需要建议波利学习打猎,因为我以前教过她一两次,但那是一场灾难。她一到达树林,就害怕了。当我打猎物时,她泪流满面,说如果我打中了猎物,我就立刻把它带回家,治好它的伤口。她养的羊真的很好,我就放她走了。
我给他们讲了我们家烧的柴火,怎么换货,怎么上学。然后我转过身,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说:“一定要听我说。你在听吗?”她点点头,被我强烈的语气吓了一跳。她也必须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你不能再离开我们了。”我说。
母亲低下了头。“我知道,我不会的。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
“好吧,但这次你得控制住。你不能抑郁,让波莉一个人呆着。现在没人能养活你了。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在电视上看到什么,你都保证坚持住!”我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在喊,声音里透露出我对她放弃一切的愤怒和恐惧。
她把搂着我的胳膊拿开,开始生自己的气。“那时我生病了。如果当时有这些药,我早就把自己治好了。”
她说她生病了,但这可能是真的。后来,我经常看到她把极度悲伤和呆滞的病人带回家。也许真的是病,只是我们负担不起。
“那就接受现实,好好照顾她!”我说。
“我会没事的,凯妮丝。”波利用手捧着我的脸说。“但你必须照顾好自己。你既敏捷又勇敢。也许你会赢。”
我赢不了,波莉心里肯定清楚。竞争激烈,超出了我的能力。富裕辖区的孩子视此为莫大的荣誉,从小就一直在接受相关的训练。男生比我大好几倍,女生也熟悉各种用刀杀人的方法。哦,当然会有我这样的人——在真正激烈的狩猎开始之前就被淘汰的人。
“也许吧,”我说。如果我早早放弃,我该怎么说服我妈坚持下去!另外,就算敌人强大,不战而退也不是我的性格。“那我们就和赫尔墨斯一样有钱了!”
“我不在乎我有没有钱,我只想让你回家。你会努力工作的,不是吗?我会努力的,对吧?”波利问道。
“一定会努力的。我发誓。”我说。我知道。我必须为波利做这件事。
这时,保安警察来到门口,示意时间到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甚至互相伤害。我嘴里一直在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两个。”他们正要说话,保安命令他们出去,并关上了门。我把头埋在天鹅绒枕头里,好像它能把我所有的烦恼都挡在外面。
又有人进来了。我抬头一看,非常惊讶。是面包店老板,皮塔·梅拉克的父亲。我不能相信他会来看我。无论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尽快杀死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他更熟悉波莉,因为波莉在矿上卖奶酪时,总会留出两块给他,他还会慷慨地给她一些面包。我们总是等他不守规矩的老婆不在了再和他交易,因为他比他老婆强多了。我相信他不会像他老婆一样,因为烤面包打儿子。但是他为什么来见我?
面包店老板尴尬地坐在一把太师椅的边缘。他是一个有着高大宽肩膀的人。他脸上有一些烧伤的疤痕,因为他常年呆在火炉旁。他一定刚刚和他的儿子道别。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纸袋,递给我。我打开纸袋,里面装着饼干。这是我们永远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谢谢你。”我说。面包店老板平时不爱多说话,此时却无言以对。"今天早上我吃了你的面包,我的朋友盖尔把它换成了一只松鼠."他点点头,好像想起了松鼠。“你受苦了。”我说。他耸耸肩,好像不太在乎。
我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了。我们只是坐着,没有说话。后来治安警察一叫,他就站了起来,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我会看好那个小女孩的,不会让她饿死的。”
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心里没那么沉重了。人们通常和我讨价还价,但他们都很喜欢波利。也许这份爱会帮助她活下来。
下一个来找我的人也是意料之外。那是三月。她没有哭也没有说再见就直接来找我了,只是急切地求我。她的语气让我吃惊。“他们让你在竞技场穿上能让你想起家乡的衣服。你能穿上这个吗?”她把那天她戴在裙子上的圆形金胸针递给了我。之前没仔细看,后来发现是一只飞鸟。
“你的胸针?”我说。我几乎从未想到要佩戴代表我们管辖范围的饰物。
“喏,要不要我给你戴上?”不等我回答,马奇俯下身来,把胸针别在我的裙子上。"答应我你会穿着它去竞技场,好吗,凯妮丝?"她说:“答应我?”
“好吧,”我说。饼干,胸针。我今天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三月也给了我一份礼物――一个脸颊上的吻。然后向左转。我心想,也许她一直是我真正的朋友。
最后,盖尔来了。也许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浪漫,但当他张开双臂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他的身体我很熟悉,他的一举一动,柴火和硝烟的味道,甚至他的心跳——这是我在寂静中打猎时听到的,现在却是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很近。
“听着,”他说,“得到一把刀很容易,但你必须找到一张弓和一支箭。那是你最好的机会。”
“他们并不总是给弓箭,”我说,心想有一年他们只提供尖头棒,各辖区的“贡品”都会被棍子打死。
“那就做一个吧,”盖尔说。“就算弓箭差,也比没有强。”
我试着按照父亲的弓箭做了一副,但是做不好。没那么容易。就算爸爸做了,有时候也是毁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找到木头,”我说。有一年,参赛者被扔到一个只有大石头、沙子和灌木丛的沙漠里。我讨厌那一年。很多玩家不是被毒蛇咬了,就是渴死了。
“几乎每次都有木头,”盖尔说。“那一年打猎游戏中有一半人冻死了,所以游戏没有娱乐性。”
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年在狩猎游戏中,我们看着玩家在晚上冻死。其实电视视频看不清楚,因为既没有柴火,也没有火把,他们只是挤在一起。卡皮特举办的比赛被认为是虎头蛇尾,所有选手都悄无声息地死去,没有打斗,也没有流血。比赛之后,通常会有生火的木材。
“是的,通常有一些木头,”我说。
“凯妮丝,这个游戏就像打猎,而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猎人。”盖尔说。
“这不仅仅是打猎。那些人有武器,有思想。”我说。
“你也有。你比他们练得多。你努力练习,”他说。“你知道怎么打猎。”
“这不是谋杀。”我说。
“这那能有多大区别?真的。”盖尔冷冷地说道。
如果我不把他们当人看,真的没什么区别,可惜,我做不到。
保安警察又来催促了。盖尔要求更多的时间,但他们强行带走了他。我心里开始发慌。
“别让他们饿着!”我拉着他的手,大声喊道。
“我不会的,你知道,我不会的!记住我,薄荷猫……”他说。这时保安警察把我们拖走了,然后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永远不知道他想让我记住什么。
从法院到火车站只有很短的车程。我从未坐过汽车,甚至马车。在“夹缝地带”,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靠走路。
我没哭是对的。火车站挤满了记者,他们手里拿着像昆虫一样的相机,对着我的脸。我面无表情。这个我练过很多次了。墙上的电视正在广播我到达火车站的消息。我看了一眼电视,看到了我冷漠的表情。我非常满意。
很明显,皮塔·梅拉克一直在流泪。有趣的是,他似乎毫不掩饰,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游戏策略。看似软弱害怕,让别人觉得他没有竞争力,然后主动出击。几年前,一个来自第七区的女孩,乔安娜·梅森,使用了这一招,并取得了成功。她一开始一直在哭,看起来像个粗心的懦夫。直到只剩下几个选手了,她才又凶又狠。她这样玩很聪明。但奇怪的是皮塔·梅拉克使用了这种战术。他是面包师的儿子。他多年来衣食无忧。他腰很粗,很强壮。如果你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就要哭一会儿了!
我们在火车门外停了几分钟,以便照相机能拍下我们。之后,我们被带到车上,车门终于在我们身后关上,火车立刻启动。
火车的速度太快了,一开始我感到窒息。除了出差,跨区域旅行是被禁止的,所以自然我没坐过火车。火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乘坐的是时速250英里的Kapit模型高速列车。我们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到达卡皮特。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建Kapit的地方原来叫“根据地”。第12区建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矿是几百年前在这里挖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矿现在都挖得很深。
在学校学到的各种知识,最终都会归结到煤矿上,基础阅读,数学,所有指导都和煤矿有关。除了每周关于泛美民族历史的课堂讲稿,这门课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感激Kapit之类的。我知道讲义后面有更多的故事,发生在那次叛乱中的真实故事。但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无论真实情况如何,都与我们能否在餐桌上找到食物无关。
“进贡”的火车包厢比法院大楼的房间还要华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个带卧室和更衣室的单间,以及一个有冷热水供应的私人浴室。在家里,我们只有自己做饭才有热水。
橱柜里装满了漂亮的衣服。艾菲特林奇告诉我,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随意穿衣服,我可以随意控制一切。离晚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脱下妈妈的蓝色裙子,洗了个热水澡。我以前从来没有洗过过热的淋浴,感觉像是下大雨,但是更热。我选了一件深绿色的外套和裤子穿上。
晚饭前的最后一刻,我突然想起了三月的金胸针。第一次好好看了一下。胸针中间是一只金色的鸟,外面有一个圆圈,只有鸟的翅膀尖与那个圆圈相连。我突然认出它是一只知更鸟。
这些鸟很有趣,是对卡波特的嘲弄。以前各个区造反卡皮特的时候,卡皮特人就养各种转基因鸟当武器。通常这些鸟被称为“杂交鸟”,或者有时简称为“杂种”。有一种鸟叫“叽叽喳喳鸟”,它能记住并重复人说过的每一句话,还能引导自己回到巢穴,尤其是雄鸟。他们被放在卡皮特敌人的藏身之处。听到信息后,鸟飞回中心通知。每个区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他们私下是怎么聊的,区里的事情是怎么传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给卡皮特发了很多假信息,卡皮特就上当了。所有的喂食中心都关闭了,这些鸟被遗弃,在野外自生自灭。
鸟儿不只是消失了。“鸣鸟”和“嘲鸟”(嘲鸟:一种嘲鸟科的新大陆鸟,尤指嘲鸟,一种产于美国南部和东部的灰白色鸟,以能模仿其他鸟的声音而闻名。通过交配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可以模仿所有鸟类的歌声和人类的歌声。虽然你不能学会清晰地说话,但你可以模仿各种声音,包括儿童的尖锐声音或男子的重低音。他们还学习唱歌,不是简单的曲调,而是多声部的复杂歌曲。如果一个人有耐心把所有的曲子都唱出来,孩子喜欢他的声音,他们一定会学的。
爸爸特别喜欢知更鸟。当我们一起打猎时,他经常吹口哨或唱复杂的曲子。经过礼貌的停顿后,知更鸟将学会唱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这样的礼遇。无论爸爸唱什么歌,所有的鸟儿都会静静地听。他的声音优美、清澈、高亢、感人,他的歌声能把人带到一种既想哭又想笑的境地。他走后,我再也无法得知他的长相。不管怎样,这只鸟给我带来了一点安慰。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他在保护我。我把别针别在衣服上。在深绿色外套的衬托下,知更鸟似乎在森林里飞翔。
艾菲·特林奇叫我去吃晚饭,我跟着她穿过摇摇晃晃的过道,这是一家被明亮的隔墙隔开的餐厅。餐厅的桌子上有许多易碎的餐具。皮塔·梅拉克正坐在那里等我们,他旁边的椅子是空的。
“爱马仕在哪里?”艾菲特林奇用明亮的声音问道。
“刚才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说要睡午觉。”皮塔说。
“是的,这是漫长的一天,”艾菲特林奇说。我想她可以放心,赫尔墨斯不在这里。谁会怪她呢?
晚餐开始了,菜一个接一个地上,先是胡萝卜汤,然后是蔬菜沙拉、羊肉丁、土豆泥、奶酪、水果和巧克力蛋糕。艾菲特林奇在吃饭的时候不断提醒我们要给肚子留点空间,还有很多好吃的。但是我吃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这么多,这么好吃。另外,如果我能在比赛前增肥几斤肉就最好了。
“至少,你的举止很得体,”我们吃完主菜时,艾菲说。“去年的两个队员用手抢饭,像野人一样。真让我反胃。”
去年的两位选手来自“裂缝地带”。他们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一旦他们吃了饭,他们当然不会在意餐桌礼仪。皮塔是面包师的儿子,我妈妈也教过我如何正确饮食。所以,当然,我会带上刀叉。但我讨厌艾菲特林奇说的话。接下来,我故意用手抓着米饭,然后用桌布擦了擦手。看到这一幕,艾菲特林奇紧闭双唇,无话可说。
吃完饭,我会努力消化的。据我所见,皮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我们的胃也适应不了这么丰富的食物。但如果我能消化格雷西·赛的老鼠肉、猪内脏和炖树皮——这是一种特殊的冬季食谱——我应该也能消化这些食物。
我们去了另一个包厢看之前在泛美的收获季节仪式的视频。当时全天滚动播放节目,可以看到整个直播过程,但只有卡皮特人才能真正看到,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丰收节仪式。
一个接一个,我们看到其他辖区的仪式,宣布选手名字,志愿者上台,更多的时候是没有志愿者。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孩子的脸。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对手。有几个人让我印象深刻。有个二区来的凶神恶煞的孩子。他跳上讲台,要求成为一名志愿者。另一个是第五区的红头发狐狸脸的女孩。还有一个十区坡脚的男生。印象最深的是11区的一个12岁女孩。她有深棕色的皮肤和眼睛。更重要的是,她在头部和动作上与波利相似。只是她上任后,有人问有没有志愿者的时候,她只能听到风吹过身边残破建筑的轰鸣声。没有人想取代她的位置。
最后播放了12区的视频。当波莉的名字被叫到时,我冲到舞台上,把波莉推到我身后。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凄厉的叫声,好像怕没人听见,把波利带走了。当然,大家都听到了。我看到盖尔把她拉开,自己走上台。对于观众拒绝鼓掌,解说员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无声的致敬。有人说12区总是有点落后,但它的风土人情是独一无二的。就在这时,赫尔墨斯从舞台上摔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皮塔的名字被抽了出来,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握了手。奏国歌。节目结束了。
艾菲特林奇不满意弄乱她假发的那部分。“你的前辈们必须学会如何上电视,以及如何在电视面前表现。”
皮塔出乎意料地笑了。“他喝醉了,”皮塔说。
“他每年都喝醉。”
“每天,”我补充道,我忍不住笑了。艾菲特林奇说话的语气很有趣,仿佛给赫尔墨斯一些建议就能纠正他的粗俗行为。
“是的,”艾菲特林奇叹了口气。“真奇怪,你们两个还觉得好笑。你要知道,前任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生命线。他会给你出主意,给你找赞助商,指定获奖礼物。爱马仕对你的生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时,赫尔墨斯跌跌撞撞地走进包厢“我错过了晚餐?”他口齿不清,吐了一地,然后倒在呕吐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