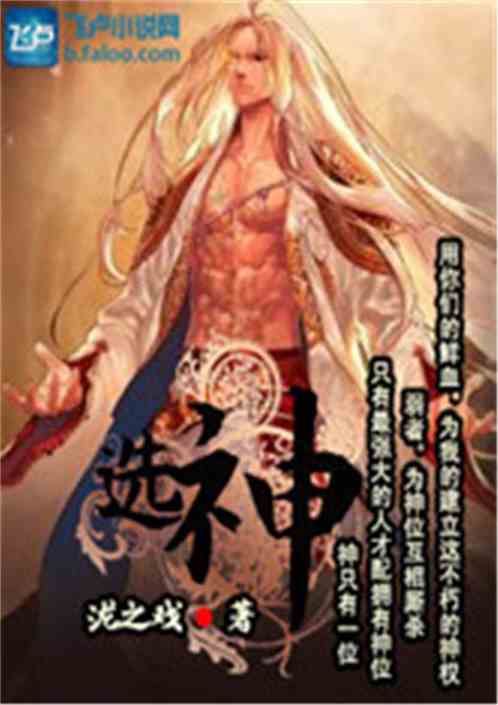《恐怖游戏》10 免费试读
皮塔说,他的脸变得忧郁起来。一瞬间,镜头对准了他耷拉着的眼皮。然后,镜头移向我。在屏幕上,我看到自己半张着嘴的表情,既叛逆又惊讶,这种表情在每一个屏幕上都被放大了,后来才知道。我吗?他是说我吗?我闭上嘴唇,盯着地板,试图隐藏自己复杂的感情。
“哦,真倒霉。”凯撒说,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真诚的痛苦。观众也在嘀咕,甚至有几个人在抽泣。
“不太好。”皮塔说。
“嗯,我想没有人会责怪你。这位年轻的女士很可爱。很难不爱上她。她不知道吗?”
皮塔摇摇头。“我想她刚刚才发现。”
我抬头看着屏幕,脸颊绯红,是的。
“难道你不想把她拉回来让她回答吗?”凯撒对观众说。观众尖叫着表示同意。“不幸的是,规则就是规则,凯妮丝·伊夫·迪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吧,祝你好运,皮塔马拉克。我想代表所有泛美人说,我们的心和你们在一起。”
观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通过表达他的爱,皮塔已经把其他人从他的道路上移走了。观众终于安静下来。他略带哽咽地轻声说了声“谢谢”,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大家起立,奏国歌。我们都必须尊重他人,高昂着头。这时,我看到每个屏幕上都有我和皮塔的照片。我们站在相隔几英尺的地方,但这个距离在每一个观众眼里从来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可怜的,悲伤的我们!
但我心里更明白这一点。
国歌之后,“致敬者”列队回到训练中心的住处,大家在电梯处集合。我小心翼翼地避开皮塔饼。人太多了。设计师,导师,女伴都掉队了。队员们面对面站着,谁也不说话。电梯停了一半,四个选手下了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到了十二楼,电梯门开了,皮塔刚从另一部电梯里出来。我上前拍了拍他的胸口。他绊了一跤,摔倒在插着假花的难看的花盆上。花盆碎了,皮塔摔在碎片上,双手立刻鲜血直流。
“你在干什么?”他惊讶地问。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没有权利说我。”我对他大喊大叫。
这时电梯到了,队员都到了。
艾菲,赫尔墨斯,西娜和鲍西娅。
“怎么了?”艾菲尖声问道:“你摔倒了吗?”
“她推的。”皮塔说艾菲和西娜扶他起来。
赫尔墨斯转向我。“你推了他?”
“这是你的主意,是不是?让我在全国人民面前变成一个傻瓜?”我回答他。
“这是我的主意,”皮塔说,拿出中间的一块。“爱马仕只是在帮我经营。”
“是的,爱马仕帮你操作。帮你。”我说。
“你真是个傻瓜。”赫尔墨斯厌恶地说道。“你认为他伤害了你?那个孩子给了你一些你自己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他让我看起来很虚弱!”我说。
“他让你很热。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你可以得到所有的帮助。在他说爱你之前,你就像灰尘,没有一丝浪漫。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你们,大家都说你们是12区的明星情侣。”赫尔墨斯说。
“但我们不是12区的明星情侣。”
赫尔墨斯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在墙上。“谁在乎?这是一场大戏,你只是给人一种感觉。面试结束了。我想说你很棒。这是一个小奇迹。现在你几乎可以说它让人流泪。哦,哦,哦,我的家乡会有多少男孩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你觉得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赞助你?”
他嘴里的酒气让我恶心。我推开他的手,坐在一边,试图理清混乱。
仙娜走过来,他搂着我的肩膀说,“他是对的,凯妮丝。”
不知道该怎么想。“他们应该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显得那么愚蠢。”我说。
“不,你做得很好。如果提前知道,就不会这么真实了。”鲍西娅说。
“她只是担心她的男朋友。”皮塔粗声粗气地说,把那块血淋淋的东西扔在一边。
一想到盖尔,我就脸红。“我没有男朋友。”
“不管怎样,”皮塔说,“我想他足够聪明,知道这只是一场表演。另外,你没说你爱我。所以,这有什么关系?”
我渐渐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我的怒气渐渐平息了,心里很矛盾。不知道是被利用了还是占了优势。赫尔墨斯是对的。我成功通过了电视面试,但那是真实的我吗?穿着漂亮裙子旋转的傻姑娘?咯咯笑,只有说到波莉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我。与苏雷什相比,他冷静有力,而我的表现却乏善可陈,愚蠢浅薄平庸。不,不是完全平庸。我的11分不算。
但是现在皮塔让我成为了仰慕的对象,而且仰慕的人不仅仅是他。据他说,我有很多崇拜者。如果观众真的认为我们是情侣…我记得观众对他的话反应有多强烈。明星爱好者。赫尔墨斯是对的。在卡波特很受欢迎。
突然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你觉得他说爱我之后我会真的爱上他吗?”我问。
“我想是的,”波西亚说。“你不敢看镜头,脸都红了。”
其他人也附和着。
“亲爱的,你现在是金牌了,赞助商会排队的,”赫尔墨斯说。
我为自己的过激行为感到非常惭愧。我强迫自己向皮塔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推你。”
“没关系,”他耸耸肩,“虽然从技术上来说这样做是违法的。”
“你的手没事吧?”我问。
“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接下来,谁也没说什么,这时一股香味从餐厅飘了出来。“来吧,我们吃饭吧,”赫密士说。我们都紧随其后,来到桌前坐下。但是皮塔在流血,波西亚带他去医务室给他包扎。先吃饭吧,第一份油玫瑰汤。直到我们吃完饭,他们才回来。皮塔的手缠着绷带,我很内疚。明天我们要去竞技场。他帮了我很多,但我却以牙还牙。我不能不欠他任何东西吗?
晚饭后,我们在客厅看了电视节目。大家都说我在电视上很迷人,但我觉得我穿裙子,打转,咯咯笑的形象很浮躁,很浅薄。而皮塔却展现出了巨大的魅力,他的表白完全赢得了观众的心。最后,我在所有人面前感到羞愧和困惑。仙娜的巧手让我美丽,皮塔的表白让我可爱,真爱无法实现的复杂局面让我难过。总之,我是难忘的。
最后,国歌奏响,节目结束,客厅陷入一片寂静。明天黎明,我们将为比赛做好准备。Kapit人起床晚,比赛要到十点才开始。但是我和皮塔必须一大早就准备好。今年比赛的场地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知道我们还要走多远。
艾菲和赫尔墨斯不会和我们一起去。他们一离开这里,就会前往比赛总部,疯狂地——我希望如此——与我们的赞助商签订合同,计划何时以及如何将礼物送到我们手中。Sina和Portia会和我们一起去场地,我们会去竞技场最后说再见。
艾菲握着我们俩的手,眼里含着泪水,祝我们一切顺利。她感谢我们,因为我们是她赞助的最好的运动员。然后,艾菲就是艾菲,通常她都要说些坏话。她说:“如果明年我升职了,被派到一个更体面的辖区,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然后她吻了吻我们的脸颊,匆匆走了出去。我很难过要离开我们,但也担心我不确定的未来。
赫尔墨斯伸出手臂,仔细地看着我们俩。
"最后有什么建议吗?"皮塔问。
“只要锣一响,你就会从这个鬼地方冲出来。不要为整个宙斯之角而死(宙斯之角,希腊神话中哺乳宙斯的角,开满了花和果实,丰富。——译者注。你要尽量远离别人散开,然后努力找水。懂了吗?”他说。
“然后呢?”我问。
“一定要活下去。”赫尔墨斯说,他在火车上给了我们同样的建议,但这次他没有喝醉,也没有笑。我们只是点点头。我们还能说什么?
当我回到房间时,皮塔留正在后面跟波西亚说话。我非常高兴。不管用什么奇怪的方式告别,都留到明天吧。我的床单已经掀起来了,但是没看到红头发的Avax。我希望我知道她的名字。我应该问她的。也许她可以写下来,或者用行动表达出来,但也许这只能导致对她的惩罚。
我洗了个澡,刷掉了金粉和化妆品,洗掉了美女特有的香味。所有的装饰只有指甲上的火焰图案。我决定留下它来提醒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凯妮丝,燃烧的女孩。也许在未来,它会给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穿上厚厚的毛绒睡衣,爬上床。五秒钟后,我意识到我是不可能睡着的。但是我真的很需要睡眠,因为在竞技场上,每当我被疲劳压垮的时候,死亡就会不请自来。
这可不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我还在盯着竞技场的地形。沙漠?沼泽?寒冷的荒野?我最想要的是树,这样我就可以躲起来,找到食物和栖身之处。总的来说是有树的,因为光秃秃的地形单调,游戏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天气呢?大赛主办方在其中设置了怎样的玄机,在节奏缓慢的情况下为比赛增添乐趣?其他“贡品”呢…………
越想睡着,越睡不着。最后,我难过得躺在床上。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怦怦直跳,呼吸急促。这房间感觉像监狱。如果我不能呼吸新鲜空气,我会再次打破一些东西。我沿着走廊跑到门口,试图爬上屋顶。门半开着,没有上锁。可能有人忘记关门了,不过没关系。电场会阻止任何试图绝望逃跑的人。而我不想逃跑,我只想透透气,我想最后看一眼天空和月亮,因为这是比赛前的最后一晚。
晚上屋顶没有灯。我赤脚一踏上瓷砖地板,就看到了他黑色的剪影,映衬着卡皮特昏暗的夜空。街上太吵了,房间里隔着厚厚的玻璃什么都听不到,音乐,歌声,汽车喇叭声。我可以从他身边溜走,他不会在噪音中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晚上的空气太清新了,我受不了再回到那个闷热的房间。说到底,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悄悄地走着,离他只有一码远,说:“你该睡一会儿了。”
他很惊讶,但没有转身。我看见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想错过这次盛会。反正是为了我们。”
我走在他身边,靠在栏杆上。宽阔的大街上人们在狂舞,我小心翼翼地眯着眼睛看着他们。"他们穿着节日服装吗?"
“谁能说得好?这里的人总是穿着奇怪。睡不着吧?”皮塔说。
“总是在想事情。”我说。
“你想念你的家人吗?”他问。
“没有,”我内疚地承认,“我想的都是和明天比赛有关的事情。当然,想他们也没用。”
这时,在楼下灯光的反射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他笨拙地抬着绑着绷带的手。
“我很抱歉弄伤了你的手。”
“没关系,凯妮丝,”他说。“反正游戏一开始我就不是别人的对手。”
“不要这么想。”我说。
“为什么不呢?这是事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给自己丢脸,不要……”他犹豫了。
“什么?”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我要为真正的我而死,你明白吗?”他问。我摇摇头。除了他自己,他还能为谁而死?
“我不想让他们改变我,变成一个和原来的我完全不同的怪物。”
我咬着嘴唇。我太刻薄了。我一直在想竞技场里有没有树,但是皮塔在想的是如何保持我自己,我纯粹的自己。
“你是说你不能杀人?”我问。
“不,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杀人,我不能不战而退。只是我想找个办法告诉卡皮特人,他们控制不了我,我也不是他们游戏中的棋子。”皮塔说。
“但你不是,我们都不是。这只是游戏规则。”
“是的,但是在这个规则中,仍然有你和我。你看不出来吗?”他坚持。
“有一点,但是...没关系,皮塔。谁在乎?”我说。
“我在乎,我是说,目前除了这个我还能在乎什么?”他生气地问,用他的蓝眼睛盯着我,寻找答案。
我不禁后退一步。“相信赫尔墨斯,活着回来。”
皮塔对我微笑,悲伤和讽刺。“嗯,谢谢你醒了,亲爱的。”
我好像被扇了一巴掌,他居然用赫尔墨斯的傲慢口吻跟我说话。
“好吧,如果你想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竞技场策划一场高尚的死亡,那是你的选择,但我想在12区度过余生。”我说。
“你这么说,我并不感到意外。”皮塔说:“如果你能活着回来,请向我母亲问好,好吗?”
“肯定。”我说着,转身离开了楼顶。
我在睡梦中度过了一整夜,想象着明天如何与皮塔马拉克最后告别。皮塔马拉克,看看他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会有多高尚。他可能会变成最凶猛的野兽。曾经有一个来自第六区的“贡品”名叫泰特斯,他杀死并吃掉了死者的心脏。他彻底变成了野人,于是组织者只好在他吃掉其他贡品的心脏之前用电击枪把他打晕,然后把他杀死的贡品的尸体运走。竞技场没有规则,但食人野人不被卡皮人接受,所以他们想尽办法避开。据说最后杀死泰特斯的雪崩是专门针对他的,唯恐最后的胜利者是个疯子。
早上没看到皮塔。天还没亮,司南就来找我,让我简单换了衣服,然后带我去了楼顶。我最后的着装和准备工作将在竞技场的地下室进行。一架直升机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我们上方,和那天我在树林里看到红发阿瓦克斯时出现的飞机一模一样。直升机上放下了一架梯子。手脚一上梯子,就觉得全身都冻僵了。一股电流把我粘到梯子上,然后梯子慢慢上升,把我送上了飞机。这个时候,我以为梯子会释放我,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然后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注射器。
“这是为了找你,凯特尼斯。你越安静,我装的越快。”她说。
还玩这个?虽然我很僵硬,但她在我前臂下植入追踪器的时候,我还是感觉了一会儿。现在,无论我去哪里,比赛组织者都能找到我的踪迹。他们不想失去一个贡品。
追踪器一安装好,梯子就放开了我。白衣女子消失了,直升机在楼顶接上了司南。一个叫Avax的人走了进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在那里我们准备了早餐。虽然我的胃还是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尽量多吃,吃的东西也没什么印象。这个时候我太紧张了,吃了煤灰也没什么感觉。唯一能让我分心的,就是飞机经过城市时窗外的风景,还有飞机上看到的旷野。这是只有鸟才能看到的景象,但鸟是自由安全的,而我却恰恰相反。
飞机飞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窗户就被遮住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接近竞技场了。直升机降落后,我和司南再次来到梯子前。这次不同的是,梯子接的是地下管道,直通地下室。我们被指示去最后的等待地点——一个准备用的小屋。在凯德,人们称之为“出发室”。在我们区,人们称之为牲畜圈,牲畜在被宰杀前呆在这里。
一切都是全新的,我将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致敬”使用这个出发室的人。竞技场是每场比赛后预留的地方。这也是卡皮特人经常光顾和度假的地方。他们经常花一个月的时间再看一遍比赛,参观地下室,甚至假装“贡品”排练当时的场景。
人们说这里的食物很棒。
当我刷牙的时候,我尽量不让我满肚子的食物溢出来。新浪把我的头发梳成标志性的长辫子,背在身后。然后有人送来衣服,每个“贡品”都一样。新浪对我的衣服没有发言权。他甚至不知道包里是什么。但他帮我穿好了衣服:内衣,纯棕色裤子,浅绿色外套,结实的棕色腰带和黑色帽衫一直垂到我的大腿根部。“这件夹克的面料设计可以体现体温,晚上可能会很冷。”他说。
靴子上套着紧身衣,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皮子很软,不像家里穿的那种。橡胶鞋底窄,带轮胎胎面,非常适合跑步。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当新浪从口袋里拿出金色知更鸟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你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你在火车上穿的绿色外套上."他说。然后我想起来我已经把它从我妈妈的衣服上拿下来,别在绿色的外套上了。
“这是你们区的吧?”
我点点头,然后把它别在我的衣服上。
“审查委员会差点没通过。有些人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武器,让你占优势,对别人不公平。但最后,还是过去了。”司南说,“一区女孩的一环失败了。戒指扭曲后,可以变成一根刺。那枚戒指有毒。她声称不知道戒指可以变形,也无法证明。但她还是失去了一些东西。好了,你准备好了,往下翻,看看你的衣服鞋子是否舒服。”
我绕着房子走了几圈,挥舞着手臂。
“对,很好,刚刚好。”
“嗯,现在没事可做,就等电话走了,”新浪说。“除非你能多吃点东西?”
我拒绝了食物,而是拿了一杯水慢慢喝,一边坐在长椅上等待。我再也不想敲指甲,咬嘴唇了,就咬着腮帮子。前几天咬的地方还没长出来。很快,我的嘴里就有了血腥味。
我预料到可能会发生什么,我的心情从紧张变成了恐惧。我可能会在一个小时内,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僵硬地死去。我的手指情不自禁地不停抚摸着那个女人前臂植入追踪器的凸起。虽然疼,但我使劲按,很快就青了。
“你想谈谈吗,凯妮丝?”司南问道。
我摇了摇头,但过了一会儿,我向司南伸出手,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一个女人轻快的声音宣布该开始了。
我还是拉着司南的手,走过去站在一块圆形金属板上。
“记住赫尔墨斯的话,跑去找水,其他一切自然就好了。”他说。
我点点头。
“记住,我不准赌博,但如果可以,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在你身上。”
“真的吗?”我轻声说。
“真的,”新浪说,他俯下身吻了吻我的额头。“祝你好运,燃烧的女孩。”
这时,一个桶状的玻璃罩从我身边落下,分开了我们紧紧的手,锡耶纳与外界隔绝了。他用手指敲了敲下巴,意思是:你要昂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