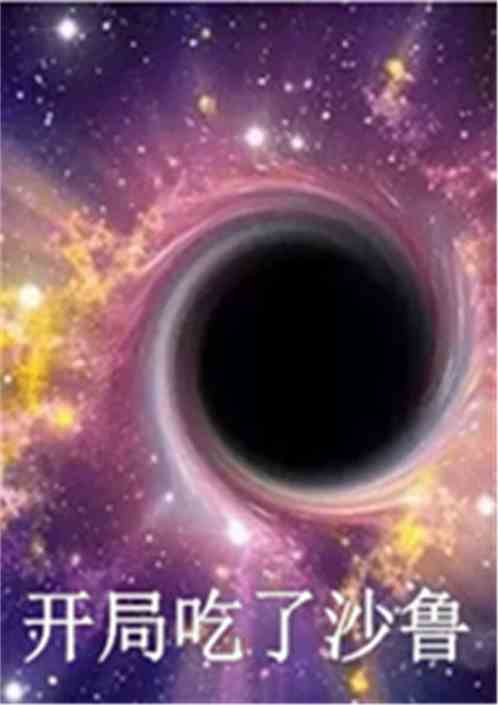空旷的土地
随着宇宙的诞生,一声尖叫宣告了虚空的开始。虚空代表了领域另一边的某种不可知的虚无。它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饥饿,等待永恒,直到它的主人和神秘的守望者发出命令,迎来一切的最终解散。
被这种力量感动,凡人可以看到永恒的幻象。同时,遭受剧烈的疼痛足以挫败最强的意志。有许多造物居住在虚空中,它们通常只有原始的认知能力,因为它们只有一个目标——彻底消灭符文区。
在这样一个只有结局和湮灭的死气沉沉的地方,声波本该被吞噬,却有一种淡然的女声。
“已经十年了。”
这种语言的发音很奇怪。如果研究过《楞严经》历史的皮尔瓦夫学者,或者相思的当地村民能听到,那就是一种流传至今的“失落的土地语言”。
早在十年前,那次事件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和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徒劳的入侵中变成了废墟。
卡奇。卡奇。
没人回答。
她听到的只有咀嚼的声音。
在畸形骨骼堆积的山上,附着在女性身上的共生甲壳渐渐消失,露出一张美丽的脸庞。
强风伴随着刺鼻的鱼腥味,撩起了女人淡紫色的头发。
卡奇。卡奇。
在女人的身边,一个魁梧的身影比其他人更高地昂着头,肌肉纤维不断被撕裂的声音从嘴里发出。
女人不生气是因为男人不理她们。与其说是和男人说话,不如说是和自己说话。她早就习惯了这种与男人相处的方式。毕竟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这个男人已经和她生活了十年。
女人抬头看着遥远的天空,但地平线上的裂缝变成了一根缝纫线,将破碎的虚空与繁星点点的夜空连接起来。不幸的是,粗糙的技术使这种奇迹的美完全消失了,或者说,只要与虚荣有关的东西就永远不会有“美”这个词。
望着裂缝,女人想起了什么,吹弹可破的翘唇微微张开,喃喃道:
"卡莎...你给我起这个名字已经十年了。”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只是一个刚刚被虚荣生物共生的小女孩。那时,我还在和Kazk系统作战。”当卡莎想到第一次遇见一个男人,冷漠的嘴角已经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意。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虚空之力,只能一拳一脚肉搏。可是,没想到你突然从天而降,打中了卡斯克部,只是让它的螳螂臂陷进了他的胸膛。”
卡奇。卡奇。
墨绿色的血从男人嘴角溢出,腥汁不小心洒在卡莎的外壳上,但一眨眼就被吸收了。
卡莎还在自言自语。
“那时候,你比我弱。你在Kazk部门摔死后,全身几乎粉骨折,嘴里老是哼哼唧唧,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但当时我已经害怕了,我以为你是某种类似人类的虚荣生物,很快就逃跑了。”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就像现在一样,躺在虚空生物的尸体上,吃着它们的血肉。”
卡莎靠在男人的背上,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天空。
“这些年来,你总是用老练的眼神警告我不要被虚荣心的能量侵蚀,但你却变成了一只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野兽。”
卡莎想一想五年前的虚无日——虚空与瓦洛兰大陆相遇的地方,没有昼夜交替,所以卡莎和男人用天空场景作为记忆这一天的时间。当天空只有虚空,相思就是白天,当虚空遇上星夜,相思就是黑夜。昼夜交替是虚无的一天。
当时这个人已经把所有虚空生物都变成了他脚下的骨头,他也因为常年吃虚空而进化。
但是因为男人吃得太干净,卡莎没有猎物可捕食,毕竟没有在虚空中储存食物的概念——虚空生物的所有尸体都不能放在虚空中超过两天的虚无中,否则它们会被虚空的力量所湮灭。
当时,卡莎刚刚来到进化的边缘,她的共生外骨骼需要大量的血肉。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男人把她带进了瘫痪状态,跑到隔壁虚空领主的区域与之战斗——一个经历了五次进化的科加斯虚空生物。
这种生物是她见过的最能进化的虚空生物。
它复杂的生物结构可以快速将物质转化为物理生长,不仅增加了肌肉的质量和密度,还使外壳像钻石一样坚硬。当单纯的体型增长已经不能满足时,这种虚空生物会将多余的物质吐出变成锋利的骨刺,刺穿猎物,为以后的盛宴做准备。
卡莎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天。整个天空都被科加斯部门的尸体覆盖了。坚硬的外骨骼直接破开了山中央,骨刺如千箭齐发,瞬间让整个空间破碎。
但是那个怪物也死在了一个人的拳头下。
它的血脂和骨髓上注射骨刺的基因也让她学会了相思中的暴雨。
卡奇。卡奇。
说这个男人让她完成进化后,她说了一些她听不懂的话,比如“浪费食物是可耻的”,然后她在两个空天里像山一样吃掉了所有的血肉,真是可笑。
但是/...
从那以后,时不时,这个人就会变成一只只会啃咬的野兽和怪物。但是即使男人变成了野兽,他也从不把她当成猎物,甚至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行为。相反,他总是在吃饭前把最有活力的部分留给她。
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她成了他的本能。
就像她喜欢看天空一样,
咀嚼食物的声音停止了,卡莎察觉到了男人身体颤抖的停止,当她站起来看着男人时,她看到了他不再浑浊的眼睛。
“叶子!你终于醒了!”
即使是卡莎,此时她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她从后面搂着那个男人坚实的手臂,正要说些什么,但她停了下来。
男人们不停地盯着远方的天空,裂缝像大口吃饭一样不断地开合,不同于虚空的能量不断地从裂缝中涌出。
这个人的嘴不停地发出野兽的咆哮,他在想十年前他是如何发音的。
最后,男人笑了。
怀着发自内心的自信,我说了我十年没说过的母语: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