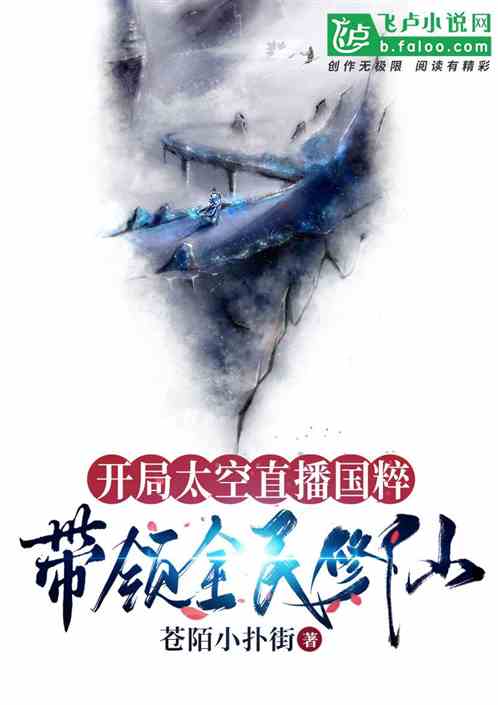“啊!你看,我们好像已经抓到船了。”吹雪惊讶地清除了海面上的漂浮物,仔细看了看新船母亲亚麻色的头发和她藏在污垢下的精致脸庞,然后说:“这就是列克星敦?”
“什么?”原本慵懒的萨拉托加突然来了精神。“姐姐?”
一把把吹来的雪推到一边,萨拉托加离开,蹲下来,仔细地看着列克星敦的脸。
吹雪生气地站起来,刚想说些什么,却被她真诚的手轻轻按在肩上,低声说:“别怪萨拉托加,她姐姐……”
“是我妹妹!”萨拉托加尖叫道:“真的是我妹妹!”
“什么?”池城觉得有点意外。
俾斯麦皱着眉头说:“真的是列克星敦吗?”
萨拉托加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声音颤抖:“当然是我妹妹。我已经找了她十年了。这件事我怎么会错!”
她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擦去莱克星顿脸上的脏脏的污垢,露出了她精致无暇的脸庞,白皙的皮肤渐渐显露出来。
最后,萨拉托加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想法。她把列克星敦抱在怀里,不停地揉她的脸,说:“姐姐,姐姐……”
威尔士亲王的表情有些复杂。她阴沉地看了一眼池城,摇了摇头,但还是没说话。
池城也抿了抿嘴唇,感觉今天有点不可思议。沉船妈妈还能再捞上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然而萨拉托加已经等了她姐姐十年了,而在这期间,叫列克星敦的船妈不在千里之外。如果她承认她姐姐的错误,人们是不会相信的。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证人可以观察了。
陈凡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的州长。
只是,提督真的能认出来吗?
在过去的十年里,只有萨拉托加在这片海域坚持不懈地等待着,提督定期来这里镇压深海。
另外,列克星敦的回归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禁压了一块大石头。
最后,俾斯麦问道:“那么,我们要把她带回府尹办公室吗?”
提督府从不接受新生的女仆。提督府作为一个机构,接受五年以上的老船娘比较多。
毕竟提督府不是镇守府,不是镇压党人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中转结构存在。
你真的想把列克星敦带回去吗?
然而萨拉托加冷冷地看了俾斯麦一眼,说:“不然呢?”
“哼!”她不满地说:“要不是我姐,我都不知道这破提督府存在!”
俾斯麦皱了皱眉,显然对萨拉托加的说法不是很满意,但她现在的心情显然不好,俾斯麦也不想多说什么。
威尔士亲王慢吞吞地说:“我觉得还是去问提督好!”"
一艘高阶舰母的压迫突然从天而降,海面被压下三分。
然而威尔士只是轻声一笑,说:“只有这样才符合规则。”她挑了挑眼角,对萨拉托加的气势视而不见。
把雪吹到一边让我难受。这是内战吗?突然觉得好危险怎么办?
她小声地问弱气,“你真的要联系政府吗?”
就在这之后,她想扇自己一巴掌,因为萨拉托加危险的眼神已经看了过来。
俾斯麦点点头说:“向提督请示是符合规定的。”
萨拉托加轻轻地把列克星敦的头放在膝盖上,稳稳地坐在起伏的海面上,说:“那就联系政府,我只想看看府尹的意见!”
她的语气很奇怪,似乎包含了很多不满。
俾斯麦看着飘飞的雪花,示意她联系。
于是吹雪立刻崩溃,用刺人的声音打开了终端,愤愤不平的选择了声音。他说:“就问提督,不是我最尴尬的事吗?他们欺负我,呜呜……”
然后,在令人不安的等待中,一个略显低沉的声音响起:“这里是提督府。有什么事吗?”
这时,在另一边,一个女声响起:“啊,提督,这是他们与吹雪的电话联系!”"
萨拉托加突然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姐姐回来了。”
另一边,提督突然愣了好久才说:“你说你妹妹回来了?”
“是的,”萨拉托加的声音略带沙哑,道,“否则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出现打扰省长和秘书长之间的调情!”
府尹咳了几声,道:“这是好事。到时候我会举行一个欢迎会。”
萨拉托加突然爆发了,压低声音说:“这就是你的态度吗,级长?”
俾斯麦不满的眼神突然飘了过来。
提督还在和那边的另一个人说话,声音传来模模糊糊的,像是“欢迎会”和“可以吗?”就像请示一样。
萨拉托加不满的声音再次响起:“提督,我妹妹到底是不是你的船妈妈?”
然后,双方都沉默了,只有海风吹拂海浪的声音,有种奇怪的寂静。
“为什么?”萨拉托加心里有点不安,说:“我妹妹不也是你们船上的提督吗?”
过了好一会儿,知府才说:“知府文书,我已经退了。”
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已经是了,还不是级长。”
萨拉托加刺耳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说什么?”
俾斯麦也皱起了眉头,真诚却震惊地看着威尔士。
“从明天起,我不再是级长了。”提督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已经没有资格做舰妈了。”
“那我呢?”萨拉托加下意识地问道。
提督沉默了。
萨拉托加·道安自己也在大惊小怪。他已经是级长的舰母了,宪兵队不会要求自己解除合同。刚才那句话真的有点尴尬。
她有点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周围的几个船妈妈。他们应该是对新闻打击最大的人。
俾斯麦淡淡地问:“提督,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你问吧。”
俾斯麦轻轻咳嗽了一声,才说:“提督,不都是为了生活吗?”为什么我没听说过退休?"
府尹苦笑了几声,道:“那是一所普通的门房。提督府从一开始就有任期,但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继承人。”
萨拉托加低下头,撅着嘴,摸着列克星敦的头发,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和姐姐当年定下的规矩。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