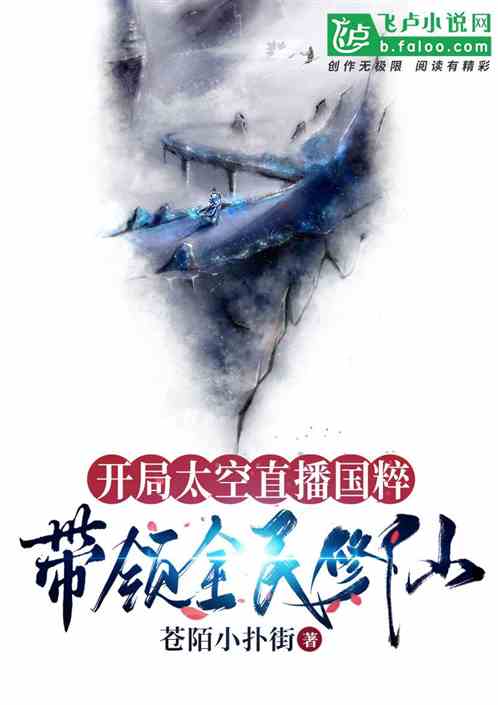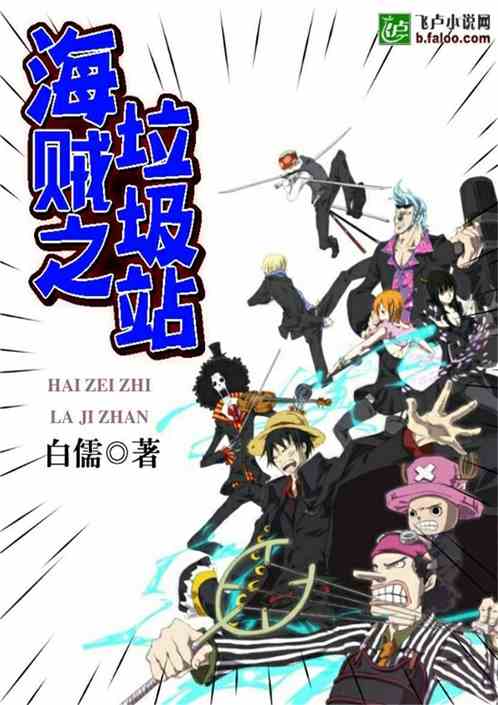黑暗的天空,黑暗的地面,黑暗的环境,一切都是黑暗的。王永桓的思想完全处于一个黑暗的空间,四周寂静凝固,没有任何波动,也没有空气。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想动却动不了。他的四肢和身体都僵硬了,就像全身麻醉一样。
荒凉、恐惧、惊吓、黑暗等一系列情绪。,像满满的液体,充斥王永桓的全身,辐射到每一个肌肤、肌肉、细胞。颤抖迷茫的思绪在黑黑的空间里飘荡游荡,就像一个没有任何依托的幽灵。
“这是在传说中的黑洞里吗?”王永桓的意识在模糊地转动。
在一个黑洞里,王永桓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在梦里,我从三岁开始的生活和学习的片段不断回放,就像一部永远播不完的电视剧,一集接一集,一幕接一幕。他的脑袋,他的大脑,塞满了如此密集而复杂的信息,以至于快要爆炸了。
不知不觉中,他发现在黑洞最远的地方,慢慢出现了一点光,像是从宇宙深处飞来的星星,越来越近,越来越亮。淡淡的暖光点,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在呼唤着带着亲情远行的儿子,安静而温暖地带回王永桓的思念。
光线不断放大,影像不断清晰,王永桓的思绪就像水中的小鱼,飘啊飘,渐行渐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暖暖的走进光里,就像回到慈母温暖的怀抱。
在我所有的思绪都进入光的那一瞬间,王永桓突然叫了一声。是恐怖吗?还是惊喜?还是回忆?他的头脑已经无法判断。
然后他突然睁开眼睛,但他痛苦地发现他的头正迅速撞上一个突出的角落。
在角落里的王永桓眼里变得越来越大,放大到极致的时候。“咣”的一声巨响,疼痛如汹涌的潮水,一下子淹没王永桓。
“妈的,我又昏迷了。”在失去意识的一瞬间,王永桓心里暗暗骂着。
但是这次王永桓没有睡着,而是被敲昏了,居然被敲昏了。十多分钟后,王永桓慢慢睁开眼睛,发出微弱的呻吟声。这才发现自己趴在了湿漉漉的地上,摆出了一个极其奇怪的姿势,就像一只煮熟的大虾,低着头,翘着脚,蜷缩在一个栅栏的角落里。
旁边放着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并排放着。说实话王永桓第一次看到这辆自行车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恐怖”。没有刹车线,没有刹车蹄,没有前后轮罩,两个踏板上只剩下光秃秃的铁杆,就像两根吃了牛奶冰的冰棍棍,突然笔直地立在空中。
至于踏板上原有的辅助设施,比如踏板上的皮,踏板两侧的皮,就像某些人的钱包一样——极其干净。
“咦,这怎么特别像我上初中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除了铃什么都响的车?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又做梦了?”
正想着这些的时候,王永桓的头突然疼了。它不仅被撞了,还被很多东西挤了,比如“草裙舞”和塞在里面的很多森碟。痛苦的王永桓眼前一黑,差点又晕了过去。
带着这种可怕的头痛站起来,王永桓看着周围的医院大墙和地上空转的自行车,他有一种恍惚和迷幻的感觉。就像这个秋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明明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怎么会突然感觉到一个成年人的沧桑和沉重?
看着万里无云的晴空,眼里的蓝色仿佛被水洗过。王永桓不由自主的嘀咕了一句“好晴朗的天空,我多少年没见过了?”
之后,王永桓自己也吓了自己一跳。“不,我从出生起就住在农场。天空一直是那么蓝。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一想到这个问题,剧烈的头痛又来了。那种刺骨的疼痛,就像几百根钢针,一起扎在我的脑海里。王永桓的痛苦搅动着我的思绪,我赶紧按下这个奇怪的念头,心里想:“算了,别想了,该回家吃饭了。”
王永桓抱起躺在地上的“车”,沿着医院的大墙走回家。一边走,他一边嘟囔着“学这自行车真的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摔了好几次,特别是这次最惨的一次,头都被打掉了。但幸运的是,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想到这里,王永桓感觉暴风雨就要来了,我立刻变得开心起来。
“日落西山夏虹飞兵打靶回营”,他们用变声射击后高高兴兴地和王永桓回家了。原本的头疼和不安,一下子被抛到了海外的地平线上。青少年没有片刻的悲伤是真的。
王永桓的家就在农场职工医院的大墙附近,只不过他家在医院的东侧,而王永桓刚好在医院的西侧撞了头。
王永桓家里的房子是红砖瓦房,在农场叫科级房。只有达到科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报考。一栋楼里有两户人家,王永桓西边一户,东边一户,姓谭,是农场的工会负责人。王永桓叫他谭大爷。
屋前有一个面积近100平方米的院子。通常在夏季种植一些豆类、茄子等国产蔬菜。房子的窗户前,有一口手摇井,用来打水做饭,浇园子里的菜。
在院子大门的东侧,王永桓又建了一个20多平米的砖房用来养牛。去年,王永桓的父亲买了一头牛,养了起来,挤牛奶赚钱,补贴家用。
牛棚旁边有一个一米多高的鸡架,里面养着一只公鸡和30多只母鸡。王永桓全家人一年的鸡蛋都是这些整天唧唧喳喳的母鸡贡献出来的,不仅够自己一家人一年四季吃,有时候剩下的还会卖掉赚点零花钱。
而且捡蛋的是王永桓,不过这小子有时候会捡鸡蛋去邻居家。每当王永桓家鸡蛋收成增加的时候,就是邻居谭大爷家鸡蛋产量减少的季节。农场工会负责人谭经常抱怨自家母鸡下蛋能力差,气得时不时抓一只来宰了喝。
这个时候,王永桓总是很兴奋。吃鸡的时候,总是不忘鼓励自己。一定要发扬捡蛋大业,保持捡蛋高产。
鸡舍旁边,用红砖搭建了一个小狗窝,王永桓家族的使者“三点”长期驻扎在此。
三是一只只有二十厘米高,五十厘米长的白色小狗。每次王永桓回家,迎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三点”。
王永桓一进大门,“三点钟”就摇头晃脑地跑了过来,直直地绕王永桓转圈、蹦蹦跳跳,小嘴一张一合,不断发出“呜呜”的欢快叫声。
王永桓弯下腰拍拍它的小脑袋。“三点,你怎么变老了?”
“啪嗒”,随意打了两下。“你自己去玩吧。”
三点,主人不想搭理它,就用小黑鼻子嗅了嗅王永桓,用白色毛绒绒的脑袋蹭了蹭裤子,然后撒欢跳了回来。
在它的窝前三点钟,又一次开始了它永无止境的游戏——绕圈追逐自己的尾巴。但是,不管它是向前转,向后转,还是转圈,都咬不到尾巴。
三分可能觉得自己速度不够快,所以咬不动。于是我更加努力,更加努力的追自己的尾巴,悲惨的结果是三点钟就晕了,晃荡到了地上。
每当王永桓看到三点追着他的尾巴咬他的时候,他就会津津有味地站在那里,看着它转圈表演,直到三点晕倒在地。但是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怪事太多了,他还没想明白是什么事。所以我没心情看三点钟的节目。抓紧一切时间进入屋子,准备继续思考那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进屋的时候,王永桓看见妈妈在厨房做饭。像往常一样,她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然后飞快地向里屋跑去。但是在喊妈妈的那一刻,王永桓心里突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又酸又痛,仿佛失去了很久的东西突然回到了我的身边,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
我妈听到小儿子叫她,就漫不经心地回答:“小三,你怎么来了?”快点洗手,一会儿吃饭。"
回到里屋,看着屋子里的物件和陈设,王永桓心里觉得好复杂,既熟悉又陌生,又开心又痛苦。我怎么会觉得这么奇怪?
王永桓房子格局是典型的农家建筑风格。进门就是一个三平米的小门斗,就像现在城市里的小门厅。
从门斗进来是一条小走廊,一米多宽,五六米长,通向尽头。走廊右手边有三个房间:第一个是厨房,七平米大小。

 已完结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