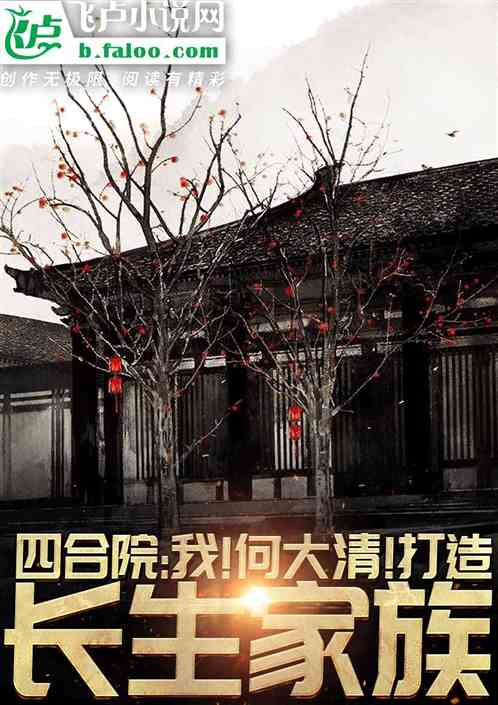1954年,大寒!
刚过完季没几天,二月的北方寒风萧瑟,鹅毛般的雪花在寒风中飘起,偌大的49城放眼望去都是一片质朴。
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前门大街的大栅栏是燕京最受欢迎的街区之一。老燕京丝绸店、瑞福祥丝绸店、直营鞋店、六必居酱菜店、荣宝斋文房四宝都是著名的老字号招牌。
“看天桥上的东西,买东西去大栅栏。”
“头顶马聚元,踩着内联,佩戴着八大吉祥,腰间佩戴着四大恒。”
这些从古至今老北平流传下来的顺口溜,讲的是北平大栅栏的商业地位和繁华景象。
一条狭长的巷道,两边都是砖墙,正下着大雪。在一家不知名的酒馆前,有一个身影躺在地上,还在任由雪花落在身上。寒冷的冬风不时吹在男人的白发上,不自觉。
酒馆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用剃须刀慢慢地刮着鬓角,有快有慢,有条不紊。没多久,长出来的小绿胡子就被彻底剃光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确认胡子刮干净后,小老头满意地点了点头。快好了,他抬起头对着酒吧的后院喊道:“惠珍,开水好了吗?”
“我来了!”一个梳着辫子的年轻女孩端着一壶热气腾腾的热水从后院走了进来。
“何叔叔,我刚刚试了试水温。天气不是很热。洗个脸正合适。”
许惠珍优雅地把干毛巾递给小老头。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你以后会嫁给永强的。我相信你能管理好这个酒馆。”
小老头接过毛巾,放在脸盆里。他开始用不太热的开水擦脸颊。刮去胡茬后,他是如此的年轻。
“何叔叔,我是有妇之夫。我就在家里结了婚,把酒馆留给永强。”许惠珍的脸变红了。虽然她做事利索,平日在老家也是落落大方,但她始终是黄花大闺女,谈婚论嫁难免有点羞涩。
“永强?”贺老头嘴角上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是冷笑。
不是他看不起养子,是对方扶不上墙。
酒馆里的客人说了几句话,就很恨不得揍对方一顿。这种态度怎么做好酒馆生意?
“得了吧,惠珍,不是我看不起我儿子,而是我以后真的得把这个酒馆给你了。”
贺老头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未来的儿媳妇许:“开酒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永强可以做一些艰苦的工作。让他当店主吧。我们还不如歇业,早日回乡种田。”
徐辉确实知道贺老头说的有道理,但毕竟是未来老公,难免要辩解一两句:“何叔叔,永强只是不习惯罢了。如果不是一直跟着父亲,经常给别人送饮料,我也不会说得这么利索。永强在酒馆待久了,我一定会是个好掌柜。”
“好吧,好吧,我知道你舍不得我谈他。”
贺老头我不怒反喜,心想我选的媳妇真是个好姑娘。有了她以后,祖辈传下来的酒馆说什么都不能黄。
“何叔叔,我来开门。”
见贺老头洗完脸,许上前拧干脸盆里的毛巾,然后提着脸盆大步走向紧闭的店门。
许刚打开门,手上的脸盆正要倒掉时,突然注意到脚下有个黑影。
往下看,小子,一个还被冰雪覆盖的死人!!!
“哦!贺叔叔不好,家里有人去世了。”
“什么?!"
贺老头房间里,只要有人死在门口,他的眼神就突然变得慌张。今天早上正要开门的时候,门口有个死人,摊开来说没事!
谁敢在我们酒馆吃饭!
扔了账本,贺老头终于看向门口,真的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旁边的许,把她吓得半死。虽然她很聪明,但她只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
不是没见过死人,只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死在我面前。
贺老头蹲下摸这个人的脖子。还有一些温度,空气中有很多酒精。
贺老头恍然大悟:“没事了,惠珍。这个人还没死。我猜他是个酒鬼。昨晚不知道去哪喝酒了。我走到我们店门口,突然就晕过去了。”
“我很高兴我没死。我很害怕。”许也就放心了。
贺老头看着路上厚厚的积雪,我有些担心,说:“死不死,但我很快就看到了。”昨晚雪下得好大,外面寒风吹了一夜。如果你不赶紧去医院,恐怕你真的忍不住了。"
“我该怎么办,何叔叔?要不我们带他去医院?”
“谁给医院钱?”
“但是……但是你不能死在我们店门口。”
许看了看贺叔叔,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她心地善良,所以不值得同情。
贺老头我本来想说可以直接扔到别处,别死在我们店门口。看得出来,我未来的媳妇是紧张的。想了想,如果我在惠珍面前说出来,总会影响我未来岳父的形象。
贺老头暗叹道:“算了,送进屋里烤吧。能不能受得了,就看他个人的运势了。”
说着,贺老头蹲下,准备背这个醉鬼。
“小子,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挺重的。”
贺老头我在工作日经常做一些重活。我能搞到一百多斤重的罐子。但是我一把这个醉鬼扛在肩上,就感觉肩膀一沉。如果我的腿和脚不整齐,我就必须倒在地上。
许见状,赶紧上前一把:“何叔叔,我来帮你。”
贺老头摆手:“不用,不用,你把后院的柴棚打开,把里屋的煤炉拿过来,顺便把我房间柜子里的两床破被子拿来。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他不可能是一家之主。”
见贺老头一个人就能做到。许惠珍点点头,走进后院。她先打开柴房的门,然后跑到里屋去拿煤炉。不一会儿,她把她订购的东西都带来了。
“何叔叔,这个人不会死吧?”
许给那人盖上被褥,看到他的脸上满是雪花。他看不清楚自己的长相,但看起来相当年轻。
“应该只剩一口气了。”
贺老头我探了探那人的鼻子,有一股淡淡的气息。
“你去倒些开水,顺便拿条旧毛巾来,我给他擦擦身子暖暖身子。如果这无法抗拒,不是我们不仗义,只是命运使然。”
“是,何叔叔。”
许前脚刚走,后脚贺老头就掀开了男人的衣服。
“好家伙,还是拉链衣服。”
“哎哟,这是羊毛的毛衣吗?”
“看起来够高档了。看不出这小子还是个有钱人。”
昏迷男的衣服和现在的平头男很不一样。它们不是老式的丝绸外套,而是一层皮革,感觉就像外面的光滑外套。里面穿的白色羊毛衫也是货真价实的好料子,不仅手感舒适,还有一种不粘手的毛线。
剥光了男人的衣服,只留下一条黑色的短裤衩。贺老头看了一眼边上脱下来的衣服:“算了吧,这套衣服搁一搁就要十几大洋。好像是救了一个富家少爷,不知道醒后能不能混点奖励。”
“何叔叔,水呢...啊!!!"
当许端着脸盆走进房间时,她看到地上的男人露出了强壮的上半身。她为自己差点没用它打翻脸盆而感到惭愧。
贺老头许闯进来的时候,她不能让儿媳妇受苦。她冲过去站在男人面前,挡住男人的身体,然后回头说:“出去,惠珍,交给我就行了。”
“是,何叔叔。”许惠真的羞愧地放下脸盆。

 已完结
已完结